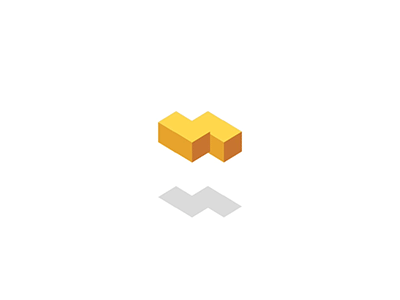+-


父 亲(二章)
潘复生
在石拐固阳一带,提起潘成义老师,人所共知。
他就学于山西五寨县立第二高小,毕业于县立一中。日本投降那年秋天,来到包头石拐,在大发窑煤矿当会计。办起石拐第一个煤矿工人夜校。
新中国成立时,石拐公忽洞村农民请潘成义当老师,学校共有十几个儿童。1952年7月,石拐开展接管改造运动,学校由民办转为公立,潘老师为自己成为新中国首批人民教师而高兴。决心实现自己的报负。
同年九月,公忽洞与白菜沟小学合并于毛忽洞,是石拐区的重点小学。摆在潘老师面前的,是一门一窗的土窑洞,三个年级复式,挤得水泄不通。他日以继夜的备课教学,批改作业。
毛忽洞村地处两条山沟交汇处,五当沟河中水流不断。夏秋天潘老师背小学生过河,冬天领着涉冰过去。遇上山洪暴发或大雪封山,他就把邻近两个村子的学生留在家中食宿,晚上给他们补习讲故事,农忙家长们有个来迟走慢,他便亲自领着学生翻山越岭送往家中。
三年后,组织上通知潘老师到更偏僻的乔圪齐小学任教。从家到学校要走五十里,翻越七八条山沟,全靠步行。四五个自然村的孩子,每天难免有一两个迟到的。他采取灵活教学方式,哪个年级学生先到齐就按课程设置给哪个年级讲,如有个别学生旷课或病耽误课程,他就在当天放学后赶到他(她)家里个别讲解。村里一些勤快的人早上起来,发现他的灯已亮了;一些晚归的人半夜回家,发现他的灯还亮着。
这盏灯,是文教科奖励他的,高座带玻璃罩的煤油灯,既是教室又是办公室又是教师宿舍的土窑洞顶上方,被油烟熏得黑乎乎一大片。
那时,上级拨给学校的经费很少。潘老师就把开始参加工作积攒下来的薪水小米卖掉,一方面补贴学校开支,一方面给穷困家庭学生订购课本和买铅笔本子。有一名姓白的蒙古族学生,母亲常年有病靠父亲一人种地养活全家五口。潘老师用自已的工资供他上学一直到小学毕业。
潘老师自己生活极其简朴节俭,一身制服穿了五年,补了又补。他见白XX隆冬数九还穿着前露脚趾后磨跟的烂布鞋,就买了一对新棉鞋给他换上。
送四年级毕业生离校时,学生们泣不成声,哽咽倾吐出一个声音:“潘老师,我们不想离开你啊!”家长们恨不得让他到高小继续跟教,他们知道这个“全区第一”成绩的来之不易和价值意义。
潘老师默默地祝愿,泪眼模糊送他们恋恋不舍离去。就在这时,文教科送奖品的同志通知他新学期到爬榆树开办小学。
经费推迟,桌橙全无。潘老师自己托土坯,在窑洞的土炕上垒起支柱,上面用锹把粗细的直木搭铺成平台,再用红胶泥拌细沙抹平,快干时用黑豆面熬的汤抹几遍。这样,就有了几排自制的平整光亮瓷实的“课桌”。上级要给几套桌凳。潘老师说:“给最需要的地方吧。”
潘老师利用空闲时间学习新东西。他听说包头马王庙小学有一相识任教,星期日凌晨三点出发,步行翻山越岭过沟爬坡,钻林踏草,到了目的地。那位老师找了一摞参考书籍,其中有民国年间课本和办学记载,外地小学典型材料,蔡元培、梁启超、胡适、朱光潜、陶行知等名家文章。潘老师如获至宝,匆匆吃饱饭告辞。回到家里,已是半夜时分。他打起精神,点亮那盏玻璃罩灯,仔细翻看阅读背回来的材料书籍,不时作些笔记。不知不觉鸡叫天亮,他用冷水洗一把脸,出门迎着朝日彩霞向学校走去。
春节,他自编书写一副对联,“榆柏绕屋绿成荫”,“花草入院籽结香”。贴在学校门上。
新学期,县里专门组织了观摩教学推广他的教学方法。
为补贴学校经费和支助穷困学生,潘老师用业余时间植树、种药、采药、养猪,把勤工俭学的收入全部用于学校和困难学生。自己分文不取。
一九六0年,国家动员精减工作人员。写了申请:从大局出发,为国分忧。人们表示遗憾,一名德高望重、优秀的教学工作者怎么被精减了?
不料就在他离开学校的时候,又被聘请为民办教师,并兼任校长,反而又挑起了重担。只是没有了1每月国家发的55元工资,由村里记九分工,按当时分值是二十几元。
父亲的遗产
父亲没有物质遗产,慌乱贫穷年代是逃难打工教书,到了追求物质的拜金主义时期,他自然成为不合时宜的老人。但他的精神却对我们影响至深。
“三年困难”时期,父亲响应国家精简公职人员号召,主动申请辞去正式教师。一个月后,公社招聘他当民办教师,待遇由每月42.5元工资变为一天十分工。面对一穷二白的乡村小学,父亲从退职金中拿出一百二十元给学校买桌凳黑板,又买了一头母猪仔和小肉猪,向生产队要了二亩荒地,搞勤工俭学。他利用业余时间种饲草料,还让母亲和我也帮着拨野菜喂猪。到冬天宰杀了肉猪,父亲用自行车驮到大磁煤矿出售,临走时母亲说:“我们也帮了不少忙,就留下一只猪蹄让娃娃们吃哇。”父亲回答:“帮忙是义务劳动做好事,应该。猪是学校的财产,咋能私自享受。”家里连一点猪油都没有沾着,全部卖掉给学校添置了教学设备。次年春天小母猪生产了八个猪仔,母亲想留一只,父亲不许,都优惠卖给本村社员,收入归了学校。母亲只好从外村买了一头小猪饲养。
我初中毕业返乡担任油坊会计后,一年下来给生产队盈利葫油六百多斤,是大师傅入库和零星支付换油长出来的。年底给社员分油时,我让父亲最后去。父亲傍晚收工后拿着家里的旧油葫芦来到油坊,按量每人一斤,我家应分八斤,我打油时装满了那个十斤的油葫芦,父亲问:“咱家应分多少?”“八斤”,我回答。父亲二话没说,把葫芦里的油倒入大油瓮让我重打。我很羞愧,只好老老实实打了八斤。父亲临走时说:“等你晚上回家再说。”下班回到家里,父亲沉着脸对我说:“你干得是什么工作?有了一点小权利就为自家谋私占便宜,怎么对得起群众和良心!”我承认了错误,保证往后再不重犯。
改革开放初期,父亲先当生产队会计后又担任了生产队长。在调整土地和分宅基地时,他完全可以“合理对付”一下,给自家弄点好的,但他一律公开透明操作,按等级顺序排好抓阄。分过来还差一亩多二等地,父亲就让先缺在自己名下,等村民们分完地要了最不好的一块河边乱荒草地,还不如社员分的三等地。以后自己一有空就挖草根刨石头、平整改良成可耕种的土地。他想得是群众,不贪不占,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。父亲常说:“做人要实实在在,办事要公公正正,为人要诚诚恳恳,工作要谨谨慎慎。”他教育我们“不要爱便宜,非己之财物一分不取,公家的东西一点不贪。”我参加工作后,还时刻叮嘱训诫,生怕又犯给自家多“分油”的错误。
晚年,父亲要我给他找一些写清官贤士的书籍和单位的旧报纸。他读着时而惋惜感叹,写一些针砭时弊抒发自己胸臆的小文章。他也和老朋友、乡亲谈论自己的看法。一些人认为潘成义“老糊涂”了,但我深知其意。他的正义、无私、诚实、勤俭精神,时刻引我自省警觉,催我奋进。成为儿女们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的精神遗产。